摘要 : 土壤修复责任的目的并非保护土地权利人,而是保护土壤不具有专属性的生态功能和维护土壤环境质量,修复责任的目的决定其属于公法责任。
《土壤污染防治法》已经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有关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追究机制的条款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条款是第48条,根据该条的规定,土壤污染责任人由农业农村、林业草原、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认定。《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分别规范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的认定。第二个条款是第97条,根据该条的规定,对于污染土壤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和组织可以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指向行政机关,针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予以起诉,起诉目的是责令行政机关履行追究修复责任的职责,这就意味着修复责任由行政机关确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者是社会组织或者检察机关,指向污染责任人,责任的确定由法院判断。由此出现了土壤修复责任追究的两种机制:一种是行政机制,一种是司法机制。责任的追究机制与责任性质是公法责任还是私法责任有关。其中的差别在于,如果土壤修复属于私法责任,责任的追究只能是司法机制;如果是公法责任,责任的追究可能是行政机制,也可能是司法机制。到底采用哪种机制,或者保留两种机制(此时需要有协调机制),需要考虑本国法律传统。从立法层面看,有必要研究土壤修复责任的性质。虽然目前《土壤污染防治法》已经施行,但作为配套规定的责任人认定办法尚未出台,责任认定依据不充分,实践中几乎没有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追究土壤修复责任的案例。在过去几年间,有关土壤修复责任的追究主要是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进行,如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振殿、马群凯水和土壤污染损害公益诉讼案,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铜仁市人民检察院诉湘盛公司、沃鑫公司土壤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许建惠、许玉仙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等。但总体而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支持的赔偿金放在法院的执行款或者当地设立的专项财政账户上也并未很好地管理并使用。赔偿金没有得到正常使用意味着环境修复没有完成。因此,在法律实践层面,运用民事框架追究土壤修复责任的困境也需要对土壤修复责任的性质进行研究和判断。
有关土壤修复责任性质的讨论,伴随着《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近几年逐渐受到关注。土壤修复经常和生态环境修复联系在一起,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加以交代。环境修复和生态修复虽然都属于生态环境修复,但二者还是存在差别。环境修复侧重于采取合理措施减轻、降低污染至可接受风险水平,而生态修复侧重于对遭受损害的生态系统的恢复;土壤修复指的是采取适当措施(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处理有害物质,降低土壤污染物至可接受水平。因而,土壤修复属于环境修复和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修复包括土壤修复。各国关于土壤修复往往有单独立法,其他领域的生态环境修复则鲜见单独立法,这体现出二者的差异。
关于生态环境修复的性质,学者观点并不一致,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李挚萍教授认为生态修复法律责任是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特别民事责任,倡导通过环境特别民事责任立法,将生态环境修复作为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主要责任方式。这种观点属于特殊私法责任说。徐以祥教授认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具有公益性和高度技术性,强调行政命令能够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中发挥重要的功能,但也承认需要建构多路径并存的救济体系,可谓持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并存说。康京涛博士则认为生态修复责任的追究工具是行政管制,行政机关可以运用公法规范监管污染者实施生态修复责任,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也有利于提高效率。巩固教授基于土壤修复的“公共责任”“法定责任”和“执法责任”等特性,认为其理应属于公法责任,而非私法责任。上述观点可谓公法责任说。笔者也曾指出土壤修复责任属于公法责任而非私法责任,应该运用行政命令追究土壤修复责任。
考虑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责任认定条款有一定的内在冲突,尤其在当下被纳入民事框架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广受关注的背景下,为避免适用上的混乱,土壤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有必要进一步廓清。尽管学者们对土壤污染责任性质的讨论有所展开,但对于责任性质的论证并不全面和系统。本文将从责任的目的面向、责任的法定强制性和专业性面向论证修复责任属于公法责任。责任的法定强制性和专业性对于责任目的而言都属于工具性保障。
| 我要评论: | |
| *内 容: |
|
| 验证码: |
|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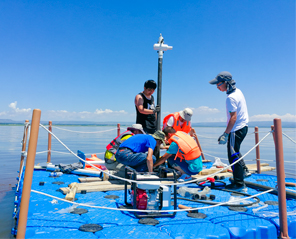



















共有-条评论